從《雷雨》的序幕和尾聲重解其主題價值的發展論文
曹禺的《雷雨》自出版以來,不斷地被人搬上舞臺,各種各樣的舞臺設計、燈光效果和環境烘托應有盡有,觀眾在演員精湛的演技中被話劇中的人物的悲歡離合感動了,被人物遭受的不堪的命運震驚了,深深地沉浸在這樣一種難以言表的悲哀中,無疑,曹禺先生的《雷雨》是一出悲劇,彰顯生命情感的脆弱不堪、人生的變幻莫測和宇宙無形的殘忍力量。但是在如今中學生的課文選講里,只是截取了一小段進行文本解讀,即使有些教師對整個戲劇進行擴展講解,也還是局限在分析人物的性格特點、釀成人物悲劇的原因、對各種社會、家庭和人物自身矛盾的剖析上。很少注意到《雷雨》戲劇的整體性效果,能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把戲劇當做一件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戲劇進行鑒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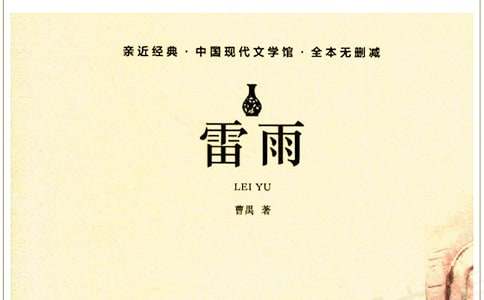
在課堂教育之外,也會發現,《雷雨》從第一次演出始,其“序幕”和“尾聲”就被刪去,此后一直沒有一個完整的演出,甚至在《雷雨》的一些文學出版物中,序幕和尾聲也都忽略不見了。曹禺對此感到非常不滿,他說:“能不能留存,主要看有否一位了解的導演精巧地搬到臺上。這個嘗試的冒險,需要導演的聰明來幫忙。”[1]在《雷雨·序》中,他寫道:“我曾經為演出‘序幕’和‘尾聲’想在那四幕里刪一下,然而思索許久,終于廢然地擱下筆,這個問題需要一位好的導演用番功夫來解決,也許有一天《雷雨》會有個新面目,經過一次合理的刪改。然而目前我將期待著好的機會,叫我依我自己的情趣來刪節《雷雨》,把它認真地搬到舞臺上。”[2]
如此看來,曹禺先生覺得序幕和尾聲在整個戲劇中是占很重要的地位的。整個序幕以教堂醫院的兩個尼姑的對話引入故事的講述,此時的周公館因為年代的久遠早已破落不堪,一片陳腐死寂。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來到療養院探望兩個病人,病人中有一個是自己的妻子,他們一個樓上,一個在樓下,老人常來但卻每次都走錯妻子的病房。而按照寺院尼姑的敘述,這其中一個婦人“大笑了一場,把玻璃又打碎了”,而另一個“哭的時候多,不說話。來了一年,沒聽見她說一句話”。這樣的寫法,一下子讓觀眾產生了好奇的心理,迫切想要了解這個周公館的曾經還有那些隨著曾經過去的人和事。在“序幕”里采用這樣的倒敘手法將一個久遠而產生了深遠影響的故事緩緩引出來,打破了戲劇“三一律”的規定,時空的轉換和結局的提前呈現卻滿足了觀眾的文學接受心理,引起了觀眾的好奇。對于這樣的開頭設計,曹禺解釋說:“我把《雷雨》做一篇詩看,一部故事讀,用‘序幕’和‘尾聲’把一件錯綜復雜的罪惡推到時間上非常遼遠的處所。因為事理變動太嚇人,里面那些隱秘不可知的東西對現在一般聰明觀眾情感上也仿佛不易明了,我乃罩上一層紗。那‘序幕’和‘尾聲’的紗幕便給了所謂‘欣賞的距離’。這樣,看戲的人們可以處在適中的地位來看戲,而不至于使情感或者理解收到了驚嚇。”[3]按照曹禺先生的說法,這“序幕”的設置實在是為了調解觀眾的心理承受能力,將它放在一個年代久遠的時間和空間里面,拉開了戲劇情節和觀眾接受心理的距離,而根據布洛的審美距離說,在審美中必須保持一定的“距離”,使得客觀現象無從與現實的自我發生勾搭,因而能使它充分顯示其本色。除此之外,在設定了這樣一層“紗幕”之后,更讓觀眾有了想象的空間,戲劇的理解也在表演的過程中得以拓展,有了更深刻、更廣泛的語境和內涵。也就是“作品是要真正地叫人思叫人想,但是,它不是叫人順著作家預先規定的思路去思,按照作家已經圈定的道路去想而是叫人縱橫自由地廣闊地去思索,去思索你所描寫的生活和人物,去思索人生,思索未來”。[4]
對于尾聲部分,文本中有一小部分是這樣描述的:
老人:(抬頭)什么?外頭又下雪了?
姑乙:(沉靜地點頭)嗯。
[老人又望一望窗前的老婦,轉身坐在爐旁的圓椅上,呆呆地望著火,這時姑乙在左邊長沙發上坐下,拿了一本圣經讀著。]
[舞臺漸暗]
如果把“序幕“和”尾聲“結合起來看,很容易發現,故事都是在教堂里發生的,在開始的時候是老人在教堂附近的醫院探望病人,而劇末尾則是在讀著《圣經》,這樣的一種開始與結尾的方式讓我們不得不重視“教堂”在戲劇中的含義,它或許不再簡單地代表一座西方建筑,這其中的人不管是繁漪還是侍萍還是那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周樸園,不管是曾經被愛煉成了魔卻依然向往自由和真情的女主人,還是一生忍氣吞聲茍延殘喘的仆人,抑或是有權有勢卻有著殘忍專制性格的資本家,都在這教堂里留下了他們的晚年,沒有了社會地位,沒有了親人孩子,沒有了余生的希望,或許,在這個雷雨天之前,他們還有著地位的懸殊,身份的壓制,不同的人生軌道,但是那個多年前的某一天里,經過了一場大雨之后,他們“同是天涯淪落人”,深深地不可挽回地沉浸在專屬于自己的悲哀中,戲劇中他們不約而同地被安排入了教堂,或許是因為在教堂的基督看來,他們之中沒有任何人是該死的,沒有任何人是該遭受這樣深重的`災難的,基督用眾生平等的博愛之心寬容了這群艱難生活的人們曾經的罪孽,讓他們在失落的余生有了一個心靈的歸宿。
當劇幕拉開,遠處教堂的合唱的彌撒聲同大風琴聲,隨著“中間門沉重地緩緩地推開”一切顯得那樣靜謐肅穆,帶著神應有的神秘和敬仰,所有的沖突、矛盾和糾纏,仿佛隨著那場雷雨的停止就悄然消解了。這一切的憤怒、悲哀還有仇恨似乎已為前世,在這里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有祥和的心境和唱詩班天堂一般的歌聲。不得不說,曹禺先生是帶著“悲憫天下”的心來從事創作的,沒有階級的對立,沒有絕對的對與錯,沒有真正的好與壞,沒有黑暗和光明,他娓娓道來一個故事的時候,悲傷已經在這個雷雨天接踵而至,但是觀眾卻來不及怨恨任何一個人,就已經聽見這局中人的困惑。人生究竟是怎樣的?人活著的意義究竟在何處?生活真的是人能夠控制的嗎?人性的深度廣度和命運的不可捉摸讓人在這個浩瀚的宇宙之間究竟在扮演怎樣的角色,處于怎樣的地位?如果原罪不可消逝,那么靈魂置于何處?似乎就像作者預計的那樣“想送看戲的人們回家,帶著一種哀靜的心情。低著頭,沉思地,念著這些在情熱、在夢想、在計算里煎熬的人們。蕩漾在他們的心里應該是水似的悲哀,流不盡的;而不是惶惑的,恐怖的,回念著《雷雨》像一場噩夢,死亡,慘痛如一只鉗子似地夾住人的心靈,喘不出一口氣來。”[5]而觀眾在看戲過程中產生的對于人生的思考,或許正是作者想要引導讀者去感受的。這也就在側面預示了《雷雨》的主題表達并不只是簡單地對封建制度的批判和對個性解放的高度歌頌。如果說曹禺先生在創作中有這樣的意圖,那也只是很膚淺的表層現象。他刻意要保留話劇的“序幕”和“尾聲”而且強調聰明的導演將它搬上舞臺,就說明這其中著重刻畫的“教堂”意義在作者的主題表達中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對人生命運未知的探索,對人生靈魂與罪孽的救贖,對人性愛恨情仇的迷茫,這些都是每個平凡人都會遇到的生存困境,這樣就把戲劇的主題意義上升到了哲學的層面,不再只是簡單地評價是非對錯,討論階級和社會矛盾。人性中的原罪意識、人生命運的變幻莫測還有精神信仰上的追尋,這些許復雜因素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巨大的思想張力,藝術審美在漸進的過程中達到了悲劇的效果,這也正是《雷雨》在一次次的演出中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參考文獻:
[1][2]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
[3][5]曹禺:《曹禺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頁.
[4]曹禺:《曹禺自述》,京華出版社 2005年版,第187 頁.
【從《雷雨》的序幕和尾聲重解其主題價值的發展論文】相關文章:
關于勞動的價值創造和價值分配的論文04-17
放飛學生心靈讓其自主發展教學論文04-23
城市給排水建設對其水資源發展的影響論文06-02
淺談學前游戲的發展價值論文05-31
反思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價值精選論文04-01
關于雷雨作解的成語解釋10-18
林業集團藍莓產業發展策略釋解論文05-01
故宮的價值與地位為主題的論文06-19
行政價值觀的形成與發展進程論文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