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東郊記憶散文
大學畢業后分配到成都,四十多年的光陰流水而過,對這座城市愈發的熱愛有加,真有點“少不入蜀,老不出川”的感嘆,也正如那句流行語“成都是一座來了就不愿離去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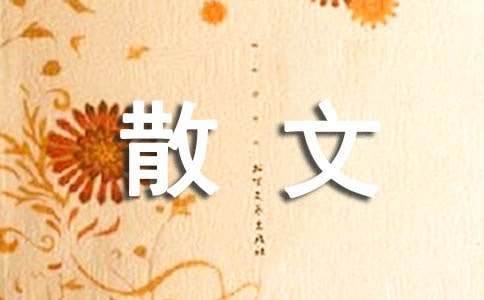
我生活的地方在成都東郊,那里曾經是成都市的老工業區,曾經聚集了解放以來興建的幾十家上萬人的大型工廠,大多是部屬的國營大型企業,分屬當時的航空部、航天部、電子部、機械部、鐵道部……。每個工廠都有自己的家屬宿舍區,有自己的學校、醫院、幼兒園、文化樓、運動場、影劇院等等,還有著名為生活供應站的各種商店和居民菜市場。
本世紀初,成都市政府實施開展“東調”戰略工程,對成都東郊老工業區內的企業實施搬遷。如今的東郊,這些工廠大多不在了,有的關門,有的搬遷到郊外。那些成片的廠房和配套建筑留下的空地,被不同的房地產開發商建成了一片片的商品房。那些原來工廠的職工,不管在職的、下崗的、離退休的,大多還在這里居住著,他們離不開這片熟悉的土地。他們大多搬了新居,有的是原單位的集資建房,有的是開發商拆遷賠償的住房,還有政府建的經濟適用房。這些住房與那些商品房,還有郊區農民被征地后的安置房,混合成了新的東郊。
幾百萬人生活的地方,需要休閑娛樂的的場所。政府順意民情,按城市工業用地更新和工業遺存保護相結合的方式,在一座大型工廠的舊址上修建了成都東區音樂公園,后來正式更名為“東郊記憶”。“東郊記憶”成為集合音樂、美術、戲劇、攝影等文化形態的多元文化園區,成為對接現代化、國際化的成都文化創意產業高地。成都東郊記憶旅游景區實現了文化創意和旅游服務的有機融合,成了市民休閑娛樂的一處好的去處。
“東郊記憶”的所在地,屬于原東郊老工業區的一部分,其前身是紅光電子管廠,該廠始建于上個世紀50年代,是“一五”期間原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之一,誕生了中國第一支黑白顯像管和第一支投影顯像管。當年,我通過紅光廠的同學從內部買搞到了一只當時十分稀缺的黑白顯像管,組裝了自己的第一臺黑白電視機,讓許多同事羨慕,也是自己的電子技術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為自己在后來的工作中參與多項利用電子技術改造設備的科技項目打下了很好的基礎,這也是我自己的東郊記憶。
我常常漫步在“東郊記憶”,昔日的老廠房已經變身為時尚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廠房里轟鳴的機器聲如今已化作各種動人的旋律,鍋爐已變成時尚的噴水池。但一走進“東郊記憶”各式場館,看著墻上懸掛的珍貴歷史影像,還有那廠房墻上還依稀可見的“抓革命促生產”之類的紅色大字標語,那一段崢嶸歲月仿佛在眼前重現。這些泛黃的照片、滾燙的文字,無言地訴說著歷史,讓大家記住為城市創造無限榮耀的開拓者與建設者。幾位老東郊帶著孫輩在一幅幅圖片前陷入沉思,久久不肯離去,他們自豪地說,大家聚在一起,看著照片,回憶建設東郊工業區的甘苦,覺得這輩子沒有虛度。是的,歲月變遷,東郊人流淌在心中的情懷依然不變。
園區里,利用舊的車間廠房,改造成了各色各樣門臉的店鋪。在古色古香的書院書店,常有作家的新書簽名發售;還有幾家畫舫畫室,常有本地畫家的畫作展覽和出售。分布著許多的小劇場,輪流開展著各式小型的音樂會、演講會和各種專業、業余的文藝演出。各種風格的咖啡廳、茶館和小吃店,恰好適合游人小歇。
我也常去“東郊記憶”的演藝中心觀看演出,演藝中心建筑面積約1萬平方米,總投資近1億元。其以典型工業廠房形式為建筑原型打造,既有工業氣息也富有現代文化潮流感,極強工業特征的室內空間令演藝大廳獨樹一格。
去年9月中下旬,“東郊記憶”戲劇季隆重舉行。李伯男導演作品《有多少愛可以胡來》紀念版再獻蓉城,在“東郊記憶”演藝中心演出,多版“胡來”演員齊聚蓉城,只為紀念我們逝去的青春,與“東郊記憶”的氛圍很是吻合!《有多少愛可以胡來》是李伯男導演的經典小劇場話劇作品,更是中國小劇場話劇歷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該劇曾在全國20多個城市演出上千場,席卷百萬人的笑聲與淚水。另一部話劇《寫給愛情的信》也在“東郊記憶”演藝中心順利演出,劇情梗概:他,相信愛情,為心中那抹不掉的記憶,任憑天涯海角也放不下掛念,但,可否心安?她,相信愛情,誰想命運連自己最后的一點期待都沒有留下,從此背上行囊拿起相機游走天涯,但,心安可否?他和她,兩個人,三十年,二百三十封信,演繹“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就是我和你……
這兩場話戲我都到現場看了,隨著劇情也悲喜交加,想起了自己在東郊的這些歲月,這里也有我青年時期的愛情,是我安家立業的地方。期待著即將在這里上演的根據巴金原作“家”改編的話劇“鳴鳳”,該劇有濃郁成都地方特色,據說四川人藝為這個劇派了很強的陣容,已經預定了票。
東郊記憶,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地方,更是一種情懷。成都東郊,這里漸漸變成了一個時髦和陌生的地方,雖然比以前的年代漂亮了很多倍,但我還是會想念以前的那些老房子,老鄰居,那個我們一起住過的東郊。我很愿意在東郊去搭乘記憶的列車,在“東郊記憶”對那些整修如舊的工業原貌中,體驗創意園區的時尚文化,回憶舊事,感悟人生。
*大地震后之隨筆
我從企業退休后被聘于一家科技公司,上班的地方在成都高新西區,就在成都繞城高速與成灌高速相交的地方,那里是成灌高速的入口,是從成都市區到都江堰風景區的主要通道。
每天清晨,我們驅車從市內經三環路轉羊西線到單位上班時,看著寬闊的道路兩旁那些高樓大廈和花園式工廠,面對這座既古老的而又現代的都市的巨大變化,心情都很不錯。
昨天是5月12日,上午天氣非常好,初夏的驕陽讓人在午后有些許疲倦。下午2時,公司管理層召開重要會議,公司老總正在布置有關公司境外上市的準備工作。會議才開了大約半小時,身下坐著的沙發突然有些輕微搖晃,接著就越搖幅度越大,桌子上的茶杯倒了,墻角的飲水機倒了。緊接著,不知是誰大喊了一聲“地震了,快跑”,大家沖出會議室加入了從辦公室沖出來的人群,一起向樓梯口跑去。
奔跑的人們,心是慌的卻不忙亂,都知道不能乘電梯,只能走樓梯。樓梯仿佛在晃動,內墻上的抹灰層一塊塊的脫落,墻上掛著的滅火器摔在地上亂滾。在下樓的過程中大家次序井然,沒有出現擁擠的現象。
當我跟隨著人流從三樓跑下到樓底,又跑到遠離高樓的花園綠地,掏出手機看了時間正好是14時30分。我抬頭看了看前面的'高樓,外墻的抹灰層已局部脫落而現出紅磚,墻體有的地方出現裂縫,掉下的水泥塊狀物將樓下停放的一輛小轎車車頭砸壞了。
這時的我,知道發生了地震,但不知道發生了多大的地震,不知道震中在哪里,不知道局面還會怎樣發展。掛念著家中親人的情況,手機卻一直打不通,沒有任何消息,心中那份牽掛難以言表。
下午3時,天空從艷陽高照變成了陰云密布。當我們驅車沿著羊西線回市內時,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堵車,進城的車多,出城的車也多。一路上看到路旁的人們,都從樓內出來集中在室外,不免心中緊緊地。但是看到市內的樓房都沒有像我們的那幢工作樓那樣出現掉灰和裂縫,我知道地震在城外而非城內人口集中處,心中才有所釋然,但也為那些身處地震中心的受災人們擔心著。
平常40分鐘的路程,那天用了兩小時才到家。到家時,通過廣播得知了消息,當天下午14:28,距離成都92公里的汶川縣發生7.8級地震,而離成都很近的都江堰市災情嚴重。我上班的那個地方就在成都到都江堰、汶川那條直線上,可以說是成都市區內離災區最近的地方了,心中不免有些后怕。
晚上不斷地收到問候的電話,都是遠方的親人、同學和友人,他們都在牽掛著處于地震區的我。由于移動通訊的堵斷,許多當天下午在災后就及時發出的問候我的短信,到了晚上我才受到。為了讓親友們放心,我都一一給與回復,因為那不是一般的短信,那都是感人至深的關愛。
這兩天,大地不時的還有時強時弱的晃動。昨天從下午到晚上,人們都不敢呆在家里,大家都在遠離樓房的空地安營扎寨。今天,隨著消息的不斷明確,人們開始平靜,生活慢慢恢復正常。
讓人得以安慰的是,全國人民都動員起來了,抗震救災的斗爭正在有序而緊張地進行。我上班那條路,正是通往災區的必經的通道,為了讓滿載著抗災人員和物資的車輛順利通行,我們公司和附近的單位都沒有上班了。
現在已經是地震的24小時以后,家中的寬帶網線剛剛恢復正常。匆忙中寫下這篇隨筆,記下地震前后的一些事,寫給關心我的朋友。就在寫這篇短文時,我在電腦桌前的椅子上感受到了兩次比較大的晃動,第一次是13:10,第二次是15:10,我知道那是兩次比較強的余震,對此我的心情已經很是平靜。
【成都東郊記憶散文】相關文章:
成都東郊記憶的心情隨筆11-05
《東郊》10-30
韋應物 東郊11-26
《東郊》韋應物10-20
韋應物《東郊》11-05
東郊韋應物09-24
韋應物:東郊09-25
韋應物 《東郊》11-13
成都印象的散文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