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 唐詩賞析
《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這首詩描作者寫貶謫放還途中游衡山,謁祭南岳,求神問卜,借以解嘲消悶,抒發對仕途坎坷的牢騷,表現對現實的冷漠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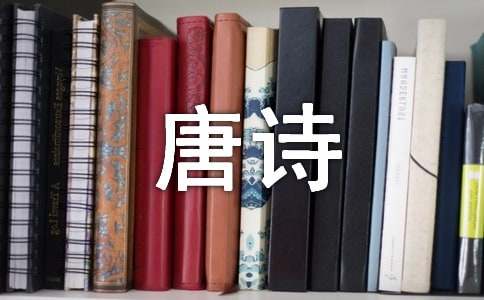
《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
作者:韓愈
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
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
噴云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
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味無清風。
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
須臾靜掃眾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
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
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徑趨靈宮。
粉墻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
升階傴僂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
廟內老人識神意,睢盱偵伺能鞠躬。
手持杯蛟導我擲,云此最吉余難同。
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長終。
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為功。
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掩映云曈昽。
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于東。
【注解】
1謁:拜見,朝拜。衡岳:南岳,即衡山,在今湖南省衡山縣。題門樓:即題詩于寺門樓上。
2五岳:即東岳泰山,西岳華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祭秩:祭祀時的等次。三公:周以太師、太保、太傅為三公,后世用以稱人臣的最高官位。
3四方環鎮:嵩山在中央,四岳環鎮四方。
4火維:指南方。地荒:荒遠的地方。足:多。
5假:授予。柄:權力。
6泄:吐出。半腹:半山腰。
7絕頂:最高峰。
8晦昧:陰暗。
9潛心:專心。默禱:暗暗禱祝。
10須臾:一會兒。掃:形容風吹干凈。
11突兀:指山峰高峻陡峭。撐:支撐。
12紫蓋、天柱:衡山峰名。
13石廩、祝融:衡山峰名。堆:高積。
14森然魄動:衡山諸峰異常高峻,望之使人驚心動魄。拜:拜謝神靈。
15靈宮:神廟。
16動:閃爍。
17青紅:指神鬼圖像的色彩。
18傴僂:彎腰,表示對神的恭敬。薦:進獻。
19菲薄:簡陋的祭品。
20睢盱:張眼為睢,閉眼為盱。睢盱在這里是偏義復詞,偏向于“睢”。偵伺:窺察。
21杯傴:占卜用具。導:指導。
22竄逐蠻荒:指韓愈被貶陽山(今在廣東)令。
23甘:心甘情愿。
24福:賜福。
25投:投宿。
26朣朧:隱約不明的樣子。
27曙:天亮。28杲杲:光明的樣子。
【韻譯】
祭祀五岳的禮儀,如同祭典三公,泰華衡恒分鎮四野,而嵩岳居中。
衡山地處荒遠的火鄉,妖怪特多,天授予南岳的權力,在那里稱雄。
噴泄的云霧,繚繞遮蔽了半山腰,雖然有橫空極頂,誰能登上頂峰。
我來這里朝拜,正逢上秋雨季節,陰暗的晦氣籠罩,沒有半點清風。
心底里默默地祈禱,仿佛有應驗,難道不是岳神正直,能感應靈通?
片刻云霧掃去,眾山峰開始顯出,抬頭仰望,山峰突兀地支撐蒼穹。
紫蓋峰連延不斷,緊接著天柱峰,石廩峰逶迤上延,綿連著祝融峰。
嚴森險峻驚心動魄,我下馬膜拜,沿著松柏間一條小徑,直奔靈宮。
白墻映襯紅柱,閃耀著奪目光彩,壁柱上圖畫模樣鬼怪,或青或紅。
登階躬背上堂,奉獻肉干和酒食,想借這菲薄祭品,表示我的虔衷。
管廟的老人,似乎知道神的旨意,凝視窺察我祭祀之意,為我鞠躬。
手里持著杯蛟,教導我如何投擲,說此卜是最吉征兆,他人難相同。
我被驅到這南蠻荒僻,僥幸不死,衣食剛足溫飽,我甘愿至死而終。
侯王將相升官欲望,我早已斷念,縱使神明要賜福于我,也難成功。
此夜投宿在佛寺,我登上了高閣,天上星月被云霧遮蔽,夜色朦朧。
猿猴啼寺鐘響,我不知天何時亮,東方升起一輪寒日,明亮又紅彤。
白話譯文
祭五岳典禮如同祭祀三公,五岳中四山環繞嵩山居中。
衡山地處荒遠多妖魔鬼怪,上天授權南岳神赫赫稱雄。
半山腰噴泄云霧迷迷茫茫,雖然有絕頂誰能登上頂峰。
我來這里正逢秋雨綿綿時,天氣陰暗沒有半點兒清風。
心里默默祈禱仿佛有應驗,豈非為人正直能感應靈通?
片刻云霧掃去顯出眾峰巒,抬頭仰望山峰突兀插云空。
紫蓋峰綿延連接著天柱峰,石廩山起伏不平連著祝融。
嚴森險峻驚心動魄下馬拜,沿著松柏小徑直奔神靈宮。
粉色墻映襯紅柱光彩奪目,壁柱上鬼怪圖畫或青或紅。
登上臺階彎腰奉獻上酒肉,想借菲薄祭品表示心虔衷。
主管神廟老人能領會神意,凝視窺察連連地為我鞠躬。
手持杯蛟教導我擲占方法,說此卜兆最吉他人難相同。
我被放逐蠻荒能僥幸不死,衣食足甘愿在此至死而終。
做侯王將相的欲望早斷絕,神縱使賜福于我也難成功。
此夜投宿佛寺住在高閣上,星月交輝掩映山間霧朦朧。
猿猴啼時鐘響不覺到天亮,東方一輪寒日冉冉升高空。
【評析】
貞元十九年(803),京畿大旱。韓愈因上書請寬民徭,被貶為連州陽山(今屬廣東)令。永貞元年(805)遇大赦,離陽山到郴州(今湖南郴縣)待命。九月,由郴州赴江陵府(今湖北江陵)任法曹參軍,途中游衡山時寫下這首詩。詩中深沉地抒發了他對仕途坎坷的不滿情懷。
衡山聳立在湖南衡陽盆地北端,氣勢雄偉。山上的衡岳廟,是游人向往的名勝。詩的開頭六句,寫衡岳的形勢和氣象,起筆高遠,用語不凡。先總敘五岳,再專敘衡岳,突出衡岳在五岳中的崇高地位。按古時帝王的祭典,五岳都相當于爵秩最高的“三公”。泰山、衡山、華山、恒山,各鎮東、南、西、北四方,而嵩山則處在中間。衡岳在炎熱而荒僻的南方,古人以為這里有很多妖魔鬼怪,天帝授予岳神權力,使它能專力雄鎮一方。詩人一連采用四個敘述句,從“五岳”寫到衡岳,竭盡鋪墊之能事。緊接二句,便一下子把衡山形勢的險要勾勒了出來:衡岳半山腰中蘊藏著云霧,不時噴泄出來,雖有山頂,又怎能攀登上去呢!一句中連用“噴”、“泄”、“藏”三個動詞,來描繪平日衡山云霧濃重不散,既奇突,又貼切。
以下八句寫登山。“我來”二句,是敘事,亦是寫景,寫出了秋雨欲來的景象,給人一種沉悶和壓抑之感。欲揚先抑,詩意推起一道波瀾。“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說衡岳有靈,使天氣由陰而晴,詩意陡轉。云霧全消,眾峰頓現,原是自然界本身的變化,而詩人卻說是自己“潛心默禱”、把正直的神明“感通”的結果。“正直”二字寓有深意。往下連用兩聯,描寫眾峰由隱而現后的景象。“須臾”一聯,寫出了山間景色變化之快:霎那之間,浮云掃盡,眾峰顯露,仰面看去,那高峻陡峭的山峰,就好比擎天柱支撐著天空。這一聯是虛寫,給人以豁然開朗、奇險明快之感。據《水經注》載:衡山有三峰,自遠望去,蒼蒼隱天。所以晉代羅含的《湘中記》也說:“望若陣云,非清霽素朝,不見其峰。”“紫蓋”一聯,描寫紫蓋峰連延著與天柱峰相接,石廩峰騰躍起伏,堆擁著祝融峰。這是實寫。汪佑《南山涇草堂詩話》說,“是登絕頂寫實景,妙用‘眾峰出’領起,蓋上聯虛,此聯實,虛實相生;下接‘森然魄動’句,復虛寫四峰之高峻,的是古詩神境。”聯系上下詩意來看,此說不無道理。
“森然”以下十四句,寫謁廟,是全詩中心所在。詩人通過對祭神問天的描述,傾吐其無處申訴的悒郁情懷。“森然”二句,點出謁衡岳廟的題意。目的地已經到達,險峻的山峰,使人驚心動魄,不由得下馬揖拜。沿著一條松柏古徑,急步走向神靈的殿堂。既反映了詩人當時肅然起敬的感受,也烘托出一種莊嚴肅穆的氣氛。“粉墻”二句,寫走進廟門后四壁所見:雪白的墻壁和朱紅的柱子,交相輝映,光彩浮動;上邊都用青紅的彩色,畫滿了鬼怪的圖像,寫出寺廟的特征。“升階”以下六句寫行祭。詩人登上臺階,彎著腰向神像進獻干肉和酒,想借這些菲薄的祭品來表明自己的虔誠。掌管神廟的老人很能了解神意,眼瞪瞪地在一旁窺察,鞠躬致禮。他手持占卜用的杯珓,教給詩人投擲的方法;而后又根據卦象,說是得到了最吉的征兆,那是其他人所不易得到的。但是,正是“云此最吉馀難同”的結語,卻引出了詩人一肚皮牢騷:自己在陽山貶所沒有被折磨致死,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今后只求衣食粗安,就甘心長此而終,哪里還存什么侯王將相之望!神明縱然想賜福保佑,恐怕也難奏效了。這一段描寫和牢騷,既真實,又動人,深刻地反映了詩人當時內心的不滿情緒。詩人關心自己的前途,當然希望占卜能得到一個非常吉利的答復。但是,當他得知是一個“最吉”的答復之后,他倒反而產生了懷疑,以致大發起牢騷來了。
末四句,歸結詩題“宿岳寺”之意。先寫上高閣時所見夜景:月色星光,因云氣掩映而隱約不明。接著翻用謝靈運“猿鳴誠知曙”句詩意(《從斤竹澗越嶺西行詩》),寫道:“猿鳴鐘動不知曙”。本來聽到猿聲啼叫就知道是天亮了,但詩人因為酣睡,連天亮時猿的啼叫聲和寺院的鐘聲都沒有聽到。詩人身遭貶謫,卻一覺睡到天明,足見襟懷之曠達。末句“寒日”,又照應上文“秋雨”、、“陰氣”,筆力遒勁。
此詩寫景、敘事、抒情,融為一體,意境開闊,章法井然。詩一開首便從大處落筆,氣勢磅礴。中間寫衡岳諸峰,突兀高聳,令人心驚魄動。求神問卜一段,亦莊亦諧,其實是詩人借以解嘲消悶。末尾數句,更清楚地反映出詩人對現實所采取的比較泠漠的態度,他對自己被貶“蠻荒”的怨憤,也溢于言表。通篇一韻到底。押韻句末尾皆用三平調(少數用“平仄平”),音節鏗鏘有力。詩的語言古樸蒼勁,筆調靈活自如,風格凝煉典重,無論意境或修辭,都獨辟蹊徑,一掃前人記游詩的陳詞濫調,正如沈德潛《唐詩別裁》所說:“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公詩足以當此語。
創作背景
此詩作于公元805年(永貞元年)。公元803年(貞元十九年),關中大旱,餓殍遍地。韓愈上書皇帝,請寬民徭,觸犯唐德宗及權貴,被貶為陽山令。公元805年(貞元二十一年)順宗即位(八月改年號為永貞),遇大赦,離陽山,到郴州等候命令。同年,憲宗登基,又議大赦,韓愈由郴州赴江陵府任法曹參軍,途中游衡山時寫下這首詩。
詩人本不信佛,這次主要是游山,但在廟令的慫恿下隨俗占卜,因為卦吉而高興。詩人迭遭不幸,對現實已經感到灰心,便借機自我解嘲。
作品鑒賞
作為文學體裁之一的詩歌,是客觀的現實生活在詩人頭腦中反映的產物。由于客觀現實和詩人境遇的不同,詩歌的藝術風格也有變化。《衡岳》和《山石》雖是出自同一手筆,且是同類題材的作品,但兩者風格明顯有別。《山石》寫得清麗飄逸,而此詩則寫得凝煉典重。
詩人通過仰望衡岳諸峰、謁祭衡岳廟神、占卜仕途吉兇和投宿廟寺高閣等情況的敘寫,抒發個人的深沉感慨,一方面為自己投身蠻荒之地終于活著北歸而慶幸,一方面對仕途坎坷表示憤懣不平,實際上也是對最高統治者的一種抗議。
開篇六句寫望岳。起筆超拔,用語不凡,突出南岳在當時眾山中的崇高地位,引出遠道來訪的原因。“我來”以下八句寫登山。來到山里,秋雨連綿,陰晦迷蒙;等到上山時,突然云開雨霽,群峰畢現。整段以秋空陰晴多變為背景,襯托出遠近諸峰突兀環立,雄奇壯觀,景象闊大,氣勢雄偉。“潛心默禱若有應”句,借衡岳有靈,引起下段祭神問天的心愿。“森然”以下十四句寫謁廟,乃全詩的核心。韓愈游南岳,雖不離賞玩名山景色,但更主要的還是想通過祭神問天,申訴無人理解、無處傾吐的悒郁情懷。在敘寫所見、所感時,肅穆之中含詼諧之語,涉筆成趣。最后四句寫夜宿佛寺。身遭貶謫,卻一覺酣睡到天明,以曠達寫郁悶,筆力遒勁。末句“寒日”,呼應“秋雨”、“陰氣”。全篇章法井然。
這首詩的思想價值雖不高,藝術表現上卻有特色。全篇寫景、敘事、抒情,融為一體,境界開闊,色彩濃重,語言古樸蒼勁,敘述自由靈活。篇幅不短,而能一韻到底,一氣呵成。雙句末尾多用三平調,少數收尾用“平仄平”,音節鏗鏘有力,重而不浮,頗具聲勢。
名家點評
《對床夜語》:《謁衡岳廟》:“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余難同。”下三字似平趁韻,而實有工于押韻者。
《黃氏日鈔》:《謁衡岳祠》,惻怛之忱,正直之操,坡老所謂“能開衡山之云”者也。
《滹南詩話》:退之《謁衡岳》詩云:“手持杯投導我擲,云此最吉余難同。”“吉”字不安,但言靈應之意可也。
《唐詩鏡》:語如鑿翠。
《批韓詩》:朱彝尊曰:二語朗快(“須臾靜掃”二句下)。此下須用虛景語點注,似更活。今卻用四峰排一聯,微覺板實(“紫蓋連延”二句下)。汪琬曰:起勢雄杰(“天假神柄”句下)。
《義門讀書記》:頂上“云霧”(“我來正逢”句下)。頂上“絕頂”(“紫蓋連延”句下)。頂上“窮”字(“松柏一徑”句下)。顧“陰晦”(“星月掩映”句下)。反照“陰氣”(末句下)。
《寒廳詩話》:韓昌黎詩句句有來歷,而能務去陳言者,全在于反用。……《岳廟》詩,本用謝靈運“猿動誠知曙”句,偏云“猿鳴鐘動不知曙”,此等不可枚舉。學詩者解得此秘,則臭腐化為神奇矣。
《唐詩別裁》:“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公詩足當此語。
《七言詩平仄舉隅》:此始以句句第五字用平矣,是阮亭先生所講七言平韻到底之正調也。蓋七古之氣局,至韓、蘇而極其致爾。
《老生常談》:昌黎《謁衡岳廟》詩,讀去覺其宏肆中有肅穆之氣,細看去卻是文從字順,未嘗矜奇好怪,如近人論詩所謂說實話也。后人遇此大題目,便以哏澀堆砌為能,去古日遠矣。“王侯將相”二句,啟后來東坡一種,蘇出于韓,此類是也。然蘇較韓更覺濃秀凌跨,此之謂善于學古,不似后人依樣葫蘆。
《昭昧詹言》:莊起陪起。此典重大題,首以議為敘,中敘中夾寫,意境詞句俱奇創,以己收。凡分三段,“森然”句奇縱。
《養一齋詩話》:退之詩“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山”,“王侯將相念久絕,神縱欲福難為功”,高心勁氣,千古無兩,詩者心聲,信不誣也。同時惟東野之古骨,可以相亞,故終身推許,不遺余力。雖柳子厚之詩,尚不引為知己,況樂天、夢得耶!
《增評韓蘇詩鈔》:三溪曰:一篇登岳,有韻記文,讀者不覺為有韻語,蓋以押韻自在,句無強押也。
《韓詩臆說》:七古中此為第一。后來惟蘇子瞻解得此詩,所以能作《海市》詩。“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曰“若有應”,則不必真有應也。我公至大至剛,浩然之氣,忽于游嬉中無心現露。“廟令老人識神意”數語,純是諧謔得妙。末云“王侯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為功”,我公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節操,忽于嬉笑中無心現露。公志在傳道,上接孟子,即《原道》及此詩可證也。文與詩義自各別,故公于《原道》、《原性》諸作,皆正言之以垂教也。而于詩中多諧言之以寫情也。即如此詩,于陰云暫開,則曰:此獨非吾正直之所感乎?所感僅此,則平日之不能感者多矣。于廟祝妄禱,則曰我已無志,神安能福我乎?神且不能強我,則平日之不能轉移于人可明矣。然前則托之開云,后則以謝廟祝、皆跌宕游戲之詞,非正言也。假如作言志詩,云我之正直,可感天地,世之勛名,我所不屑,則膚闊而無昧矣。讀韓詩與讀韓文迥別,試按之,然否?
《山涇草堂詩話》:竹咤批(按指朱彝尊評“紫蓋連延”二句語),余意不謂然。是登絕頂寫實景,妙用“眾峰出”領起。蓋上聯虛,此聯實,虛實相生。下接“森然魄動”句,復虛寫四峰之高峻,的是占詩神境。朗誦數過,但見其排蕩,化堆垛為煙云,何板實之有?首六句從五岳落到衡岳,步驟從容,是典制題開場大局面,領起游意。“我來正逢”十二句,是登衡岳至廟寫景。“升階傴僂”六句敘事。“竄逐蠻荒”四句寫懷。“夜投佛寺”四句結宿意。精警處在寫懷四句。明哲保身,是圣賢學問,隱然有敬鬼神而遠之意。廟令老人,目為尋常游客,寧非淺視韓公?
《唐宋詩舉要》:吳曰:此東坡所謂“能開衡山之云”者,最足見公之志節。此詩質健,乃韓公本色。
英漢對照
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
韓愈
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
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雄。
噴云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
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
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
須臾靜掃眾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
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
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逕趨靈宮。
紛墻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填青紅。
升階傴僂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
廟內老人識神意,睢盱偵伺能鞠躬。
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余難同。
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長終。
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為功。
夜投佛寺上高閣,星月掩映云曈昽。
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于東。
STOPPING AT A TEMPLE ON HENG MOUNTAIN I INSCRIBE THIS POEM IN THE GATE-TOWER
Han Yu
The five Holy Mountains have the rank of the Three Dukes.
The other four make a ring, with the Song Mountain midmost.
To this one, in the fire-ruled south, where evil signs are rife,
Heaven gave divine power, ordaining it a peer.
All the clouds and hazes are hidden in its girdle;
And its forehead is beholden only by a few.
...I came here in autumn,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When the sky was overcast and the clear wind gone.
I quieted my mind and prayed, hoping for an answer;
For assuredly righteous thinking reaches to high heaven.
And soon all the mountain-peaks were showing me their faces;
I looked up at a pinnacle that held the clean blue sky:
The wide Purple-Canopy joined the Celestial Column;
The Stone Granary leapt, while the Fire God stood still.
Moved by this token, I dismounted to offer thanks.
A long path of pine and cypress led to the temple.
Its white walls and purple pillars shone, and the vivid colour
Of gods and devils filled the place with patterns of red and blue.
I climbed the steps and, bending down to sacrifice, besought
That my pure heart might bewelcome, in spite of my humble offering.
The old priest professed to know the judgment of the God:
He was polite and reverent, making many bows.
He handed me divinity-cups, he showed me how to use them
And told me that my fortune was the very best of all.
Though exiled to a barbarous land, mine is a happy life.
Plain food and plain clothes are all I ever wanted.
To be prince, duke, premier, general, was never my desire;
And if the God would bless me, what better could he grant than this ? --
At night I lie down to sleep in the top of a high tower;
While moon and stars glimmer through the darkness of the clouds....
Apes call, a bell sounds. And ready for dawn
I see arise, far in the east the cold bright sun.
作者簡介
韓愈(768—824),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字退之,河南南陽(今河南孟州)人。因其常據郡望自稱昌黎韓愈,故后世稱之為韓昌黎;卒謚“文”,世稱韓文公。公元792年(貞元八年)進士及第,曾任國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職,官至吏部侍郎。在政治上反對藩鎮割據,在文學上主張文以載道,其散文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并稱“韓柳”。詩與孟郊并稱“韓孟”。其詩力求新奇,有時流于險怪,對宋詩影響頗大。有《昌黎先生集》。
【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 唐詩賞析】相關文章:
唐詩《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08-16
唐詩《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詩意賞析09-06
《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08-26
韓愈《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賞析09-01
韓愈的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賞析08-02
《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韓愈08-09
《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韓愈唐詩鑒賞08-24
韓愈《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