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汪曾祺小說《日規》
引導語:大家知道什么是日規,它是利用太陽投射的影子來測定時刻的裝置。那么下文的小說《日規》大家知道?是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汪曾祺的小說,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原文,與大家分享學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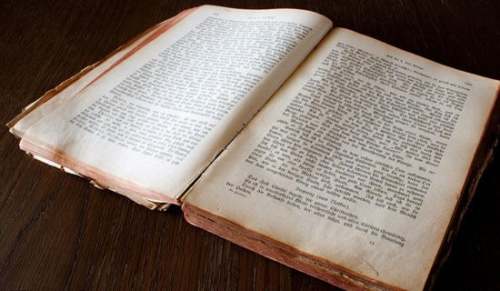
西南聯大新校舍對面是“北院”。北院是理學院區。一個狹長的大院,四面有夯土版筑的圍墻。當中是一片長方形的空場。南北各有一溜房屋,土墻,鐵皮房頂,是物理系、化學系和生物系的辦公室、教室和實驗室。房前有一條土路,路邊種著一排不高的尤加利樹。一覽無余,安靜而不免枯燥。這里不像新校舍一樣有大圖書館、大食堂、學生宿舍。教室里沒有風度不同的教授講授各種引人入勝的課程,墻上,也沒有五花八門互相論戰的壁報,也沒有尋找失物或出讓衣物的啟事。沒有操場,沒有球賽。因此,除了理學院的學生,文法學院的學生很少在北院停留。不過他們每天要經過北院。由正門進,出東面的側門,上一個斜坡,進城墻缺口。或到“昆中”、“南院”聽課,或到文林街坐茶館,到市里閑逛,看電影……理學院的學生讀書多是比較扎實的,不像文法學院的學生放浪不羈,多少帶點才子氣。記定理、抄公式、畫細胞,都要很專心。因此文學院的學生走過北院時都不大聲講話,而且走得很快,免得打擾人家。但是他們在走盡南邊的土路,將出側門時,往往都要停一下:路邊開著一大片劍蘭!
這片劍蘭開得真好!是美國種。別處沒有見過。花很大,比普通劍蘭要大出一倍。什么顏色的都有。白的、粉的、桃紅的、大紅的、淺黃的、淡綠的、藍的、紫得像是黑色的。開得那樣旺盛,那樣水靈!可是,許看不許摸!這些花誰也不能碰一碰。這是化學系主任高崇禮種的。
高教授是個出名的嚴格方正、不講情面的人。他當了多年系主任,教普通化學和有機化學。他的為人就像分子式一樣,絲毫通融不得。學生考試,不及格就是不及格。哪怕是考了59分,照樣得重新補修他教的那門課程。而且常常會像訓小學生一樣,把一個高年級的學生罵得面紅耳赤。這人整天沒有什么笑容,老是板著臉。化學系的學生都有點怕他,背地里叫他高閻王。他除了科學,沒有任何娛樂嗜好。不抽煙。不喝酒。教授們有時湊在一起打打小麻將,打打橋牌,他絕不參加。他不愛串門拜客閑聊天。可是他愛種花,只種一種:劍蘭。
這還是在美國留學時養成的愛好。他在麻省理工學院讀化學。每年暑假,都到一家專門培植劍蘭的花農的園圃里去做工,掙取一學年的生活費用,因此精通劍蘭的種植技術。回國時帶回了一些花種,每年還種一些。在北京時就種。學校遷到昆明,他又帶了一些花種到昆明來,接著種。沒想到昆明的氣候土壤對劍蘭特別相宜,花開得像美國那家花農的園圃里的一般大。逐年發展,越種越多,長了那樣大一片!
可是沒有誰會向他要一穗花,因為都知道高閻王的脾氣:他的花絕不送人。而且大家知道,現在他的花更碰不得,他的花是要賣錢的!
昆明近日樓有個花市。近日樓外邊,有一個水泥砌的圓池子。池子里沒有水,是干的。賣花的就帶了一張小板凳坐在池子里,把各種鮮花攤放在池沿上賣。晚香玉、緬桂花、康乃馨,也有劍蘭。池沿上擺得滿滿的,色彩繽紛,老遠地就聞到了花香。昆明的中產之家,有買花插瓶的習慣。主婦上街買菜,菜籃里常常一頭放著魚肉蔬菜,一頭斜放著一束鮮花。花菜一籃,使人感到一片盎然的生意。高教授有一天走過近日樓,看看花市,忽然心中一動。
于是他每天一清早,就從家里走到北院,走進花圃,選擇幾十穗半開的各色劍蘭,剪下來,交給他的夫人,拿到近日樓去賣。他的劍蘭花大,顏色好,價錢也不太貴,很快就賣掉了。高太太就喜吟吟地走向菜市場。來時一籃花,歸時一籃菜。這樣,高教授的生活就提高了不少。他家的飯桌上常見葷腥。星期六還能燉一只母雞。云南的玉溪雞非常肥嫩,肉細而湯清。高太太把剛到昆明時買下的,已經棄置墻角多年的汽鍋也洗出來了。劍蘭是多年生草本,全年開花;昆明的氣候又是四季如春,不缺雨水,于是高教授家汽鍋雞的香味時常飄入教授宿舍的左鄰右舍。他的兩個在讀中學的兒女也有了比較整齊的鞋襪。
哪位說:教授賣花,未免欠雅。先生,您可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您不知道抗日戰爭期間,大后方的教授,窮苦到什么程度。您不知道,一位國際知名的化學專家,同時又是對社會學、人類學具有廣博知識的才華橫溢而性格(在有些人看來)不免古怪的教授,穿的是一雙“空前絕后”的布鞋——腳趾和腳跟部位都磨通了。中文系主任,當代散文大師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他就買了一件云南趕馬人穿的粗毛氆氆一口鐘穿在身上御寒,樣子有一點像傳奇影片里的俠客,只是身材略嫌矮小。原來抽笳立克、35牌香煙的教授多改成抽煙斗,抽本地出的鹿頭牌的極其辛辣的煙絲。他們的3B煙斗的接口處多是破裂的、纏著白線。有些著作等身的教授,因為家累過重,無暇治學,只能到中學去兼課。有個治古文字的學者在南紙站掛筆單為人治印。有的教授開書法展覽會賣錢。教授夫人也多想法掙錢,貼補家用。有的制作童裝,代織毛衣毛褲,有幾位哈佛和耶魯畢業的教授夫人,集資制作西點,在街頭設攤出售。因此,高崇禮賣花,全校師生,皆無非議。
大家對這一片劍蘭增加了一層新的看法,更加不敢碰這些花了。走過時只是遠遠地看看,不敢走近,更不敢停留。有的女同學想多看兩眼,另一個就會說:“快走,快走!高閻王在辦公室里坐著呢!”沒有誰會想起干這種惡作劇的事,半夜里去偷掐高教授的一穗花。真要是有人掐一穗,第二天早晨,高教授立刻就會發現。這花圃里有多少穗花,他都是有數的。
只有一個人可以走進高教授的花圃,蔡德惠。蔡德惠是生物系助教,坐辦公室。生物系辦公室和化學系辦公室緊挨著、門對門。蔡德惠和高教授朝夕見面,關系很好。
蔡德惠是一個非常用功的學生。從小學到大學,各門功課都很好。他生活上很刻苦,聯大四年,沒有在外面兼過一天差。
聯大學生的家大都在淪陷區。自從日本人占了越南,滇越鐵路斷了,昆明和平津滬杭不通郵匯,這些大學生就斷絕了經濟來源。教育部每月給大學生發一點生活費,叫做“貸金”。“貸金”名義上是“貸”給學生的,但是誰都知道這是永遠不會歸還的。這實際上是救濟金,不知是哪位聰明的官員想出了這樣一個新穎別致的名目,大概是覺得救濟金聽起來有傷大學生的尊嚴。“貸金”數目很少,每月十四元。貨幣貶值,物價飛漲,這十四元一直未動。這點“貸金”只夠交伙食費,所以聯大大部分學生都在外面找一個職業。半工半讀,對付著過日子。五花八門,干什么的都有。有的在中學兼課,有的當家庭教師。昆明有個冠生園,是賣廣東飯菜點心的。這個冠生園不知道為什么要辦一個職工夜校,而且辦了幾年,聯大不少同學都去教過那些廣東名廚和糕點師傅。有的到西藥房或拍賣行去當會計。上午聽課,下午坐在柜臺里算帳,見熟同學走過,就起身招呼談話。有的租一間門面,修理鐘表。有一位坐在郵局門前為人寫家信。昆明有一個古老的習慣,每到正午時要放一炮,叫做“放午炮”。據說每天放這一炮的,也是聯大的一位貴同學!這大概是哪位富于想象力的聯大同學造出來的謠言。不過聯大學生遍布昆明的各行各業,什么都干,卻是事實。像蔡德惠這樣沒有兼過一天差的,極少。
聯大學生兼差的收入,差不多全是吃掉了。大學生的胃口都極好:都很饞。照一個出生在南洋的女同學的說法,這些人的胃口都“像刀子一樣”,見什么都想吃。也難怪這些大學生那么饞,因為大食堂的伙食實在太壞了!早晨是稀飯,一碟炒蠶豆或豆腐乳。中午和晚上都是大米干飯,米極糙,顏色紫紅,中雜不少沙粒石子和耗子屎,裝在一個很大的木桶里。盛飯的杓子也是木制的。因此飯粒入口,總帶著很重的松木和楊木的氣味。四個菜,分裝在淺淺的醬色的大碗里。經常吃的是煮蕓豆;還有一種不知是什么原料做成的紫灰色像是鼻涕一樣的東西,叫做“魔芋豆腐”。難得有一碗炒豬血(昆明叫“旺子”),幾片炒回鍋肉,這種淡而無味的東西,怎么能滿足大學生們的刀子一樣的食欲呢?二十多歲的人,單靠一點淀粉和碳水化合物是活不成的,他們要高蛋白,還要適量的動物脂肪!于是聯大附近的小飯館無不生意興隆。新校舍的圍墻外面出現了很多小食攤。這些食攤上的食品真是南北并陳,風味各別。最受歡迎的是一個廣東老太太賣的雞蛋餅:雞蛋和面,入鹽,加大量蔥花,于平底鍋上煎熟。廣東老太太很舍得放豬油,餅在鍋里煎得嗞嗞地響,實在是很大的誘惑。煎得之后,兩面焦黃,徑可一尺,卷而食之,極可解饞。有一家做一種餅,其實也沒有什么稀奇,不過就是加了一點白糖的發面餅,但是是用松毛(馬尾松的松葉)烤熟的,帶一點清香,故有特點。聯大的女學生最愛吃這種餅。昆明人把女大學生叫做“摩登”,于是這種餅就被叫成“摩登”耙耙。這些“摩登”們常把一個耙耙切開,中夾叉燒肉四兩,一邊走,一邊吃,絲毫不覺得有什么不文雅。有一位貴州人每天挑一副擔子來賣餛飩面。他賣餛飩是一邊包一邊下的。有時餛飩皮包完了,他就把餛飩餡一小疙瘩一小疙瘩撥到湯里下面。有人問他:“你這叫什么面?”這位貴州老鄉毫不猶豫地答曰:“桃花面!”……
蔡德惠偶爾也被人拉到米線鋪里去吃一碗悶雞米線,但這樣的時候很少。他每天只是吃食堂。吃煮蕓豆和“魔芋豆腐”。四年都是這樣。
蔡德惠的衣服倒是一直比較干凈整齊的。
聯大的學生都有點像是陰溝里的鵝——顧嘴不顧身。女同學一般都還注意外表。男同學里西服革履,每天把褲子脫下來壓在枕頭下以保持褲線的,也有,但是不多。大多數男大學生都是不衫不履,邋里邋遢。有人褲子破了,找一根白線,把破洞處系成一個疙瘩,只要不露肉就行。蔡德惠可不是這樣。
蔡德惠四五年來沒有添置過什么衣服,——除了鞋襪。他的衣服都還是來報考聯大時從家里帶來的。不過他穿得很仔細。他的衣服都是自己洗,而且換洗得很勤。聯大新校舍有一個文嫂,專給大學生洗衣服。蔡德惠從來沒有麻煩過她。不但是衣服,他連被窩都是自己折洗,自己做。這在男同學里是很少有的。因此,后來一些同學在回憶起蔡德惠時,首先總是想到蔡德惠在新校舍一口很大的井邊洗衣裳,見熟同學走過,就抬起頭來微微一笑。他還會做針線活,會裁會剪。一件襯衫的肩頭穿破了,他能拆下來,把下擺移到肩頭,倒個個兒,縫好了依然是一件完整的襯衫,還能再穿幾年。這樣的活計,大概多數女同學也干不了。
也許是性格所決定,蔡德惠在中學時就立志學生物。他對植物學尤其感興趣。到了大學三年級,就對植物分類學著了迷。植物分類學在許多人看來是一門很枯燥的學問,單是背那么多拉丁文的學名,就是一件叫人頭疼的事。可是蔡德惠覺得樂在其中。有人問他:“你干嘛搞這么一門干巴巴的學問?”蔡德惠說:“干巴巴的?——不,這是一門很美的科學!”他是生物系的高材生。四年級的時候,系里就決定讓他留校。一畢業,他就當了助教,坐辦公室。
高崇禮教授對蔡德惠很有好感。蔡德惠算是高崇禮的學生,他選讀過高教授的普通化學。蔡德惠的成績很好,高教授還記得。但是真正使高教授對蔡德惠產生較深印象,是在蔡德惠當了助教以后。蔡德惠很文靜。隔著兩道辦公室的門,一天幾乎聽不到他的聲音。他很少大聲說話。干什么事情都是輕手輕腳的,絕不會把桌椅抽屜搞得乒乓亂響。他很勤奮。每天高教授來剪花時候(這時大部分學生都還在高臥),發現蔡德惠已經坐在窗前低頭看書,做卡片。雖然在學問上隔著行,高教授無從了解蔡德惠在植物學方面的造詣,但是他相信這個年輕人是會有出息的,這是一個真正做學問的人。高教授也聽生物系主任和幾位生物系的教授談起過蔡德惠,都認為他有才能,有見解,將來可望在植物分類學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高教授對這點深信不疑。因此每天高教授和蔡德惠點頭招呼,眼睛里所流露的,就不只是親切,甚至可以說是:敬佩。
高教授破例地邀請蔡德惠去看看他的劍蘭。當有人發現高閻王和蔡德惠并肩站在這一片華麗斑斕的花圃里時,不禁失聲說了一句:“這真是黃河清了!”蔡德惠當然很喜歡這些異國名花。他時常擔一擔水來,幫高教授澆澆花;用一個小薅鋤松松土;用煙葉泡了水除治劍蘭的膩蟲。高教授很高興。
蔡德惠簡直是釘在辦公室里了,他很少出去走走。他交游不廣,但是并不孤僻。有時他的杭高老同學會到他的辦公室里來坐坐,——他是杭州人,杭高(杭州高中)畢業,說話一直帶著杭州口音。他在新校舍同住一屋的外系同學,也有時來。他們來,除了說說話,附帶來看蔡德惠采集的稀有植物標本。蔡德惠每年暑假都要到滇西、滇南去采集標本。像木蝴蝶那樣的植物種子,是很好玩的。一片一片,薄薄的,完全像一個蝴蝶,而且一個莢子里密密的擠了那么多。看看這種種子,你會覺得:大自然真是神奇!有人問他要兩片木蝴蝶夾在書里當書簽,他會欣然奉送。這東西滇西多的是,并不難得。
在蔡德惠那里坐了一會的同學,出門時總要看一眼門外朝南院墻上的一個奇怪東西。這是一個日規。蔡德惠自己做的。所謂“做”,其實很簡單,找一點石灰,跟瓦匠師傅借一個抿子,在墻上抹出一個規整的長方形,長方形的正中,垂直著釘進一根竹筷子,——院墻是土墻,是很容易釘進去的。筷子的影子落在雪白的石灰塊上,隨著太陽的移動而移動。這是蔡德惠的鐘表。蔡德惠原來是有一只懷表的,后來壞了,他就一直沒有再買,——也買不起。他只要看看筷子的影子,就知道現在是幾點幾分,不會差錯。蔡德惠做了這樣一個古樸的日規,一半是為了看時間,一半也是為了好玩,增加一點生活上的情趣。至于這是不是也表示了一種意思:寸陰必惜,那就不知道了。大概沒有。蔡德惠不是那種把自己的決心公開表現給人看的人。不過凡熟悉蔡德惠的人,總不免引起一點感想,覺得這個現代古物和一個心如古井的青年學者,倒是十分相稱的。人們在想起蔡德惠時,總會很自然地想起這個日規。
蔡德惠病了。不久,死了。死于肺結核。他的身體原來就比較孱弱。
生物系的教授和同學都非常惋惜。
高崇禮教授聽說蔡德惠死了,心里很難受。這天是星期六。吃晚飯了,高教授一點胃口都沒有。高太太把汽鍋雞端上桌,汽鍋蓋噗噗地響,汽鍋雞里加了宣威火腿,噴香!高崇禮忽然想起: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雞湯,他也許不會死!這一天晚上的汽鍋雞他一塊也沒有吃。
蔡德惠死了,生物系暫時還沒有新的助教遞補上來,生物系主任難得到系里來看看,生物系辦公室的門窗常常關鎖著。
蔡德惠手制的日規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舊在慢慢地移動著。
一九八四年六月五日初稿,六月七日重寫。
汪曾祺語錄
1、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
2、初陽照積雪,色如胭脂水。
3、坐在亭子里,覺山色皆來相就。
4、山家除夕無他事,插了梅花便過年。
5、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
6、紫蘇葉子上的紅色呵,暑假快過去了。
7、許多東西吃不慣,吃吃,就吃出味兒來了。
8、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菰湯,我想念家鄉的雪。
9、在黑白里溫柔地愛彩色,在彩色里朝圣黑白。
10、我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只我這里一點是熱的。
11、我以為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生活的抒情詩。
12、無聊是對欲望的欲望,我的孤獨是認識你的孤獨。
13、人間存一角,聊放側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
14、我則有點像董日鑄,以為“濃、熱、滿三字盡茶理”。
15、隆冬風厲,百卉凋殘,晴窗坐對,眼目增明,是歲朝樂事。
16、帶著雨珠的緬桂花使我的心軟軟的,不是懷人,不是思鄉。
17、我舍不得你,但是我得走。我們,和你們人不一樣,不能湊合。
18、每當家像一個概念一樣浮現于我的記憶之上,它的顏色是深沉的。
19、有毛的不吃撣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葷不吃死人,小葷不吃蒼蠅。
20、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納外來于傳統,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作者: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蘇省高郵市,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后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對戲劇與民間文藝也有深入鉆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畢業考入江陰縣南菁中學讀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聯主辦的《北京文藝》編輯。1961年冬,用毛筆寫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發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異秉》在《雨花》發表。1996年12月,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推選為顧問。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點30分因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77歲。
【汪曾祺小說《日規》】相關文章:
汪曾祺小說《故里雜記》04-07
汪曾祺小說《晚飯花》04-07
汪曾祺小說《王全》04-24
汪曾祺小說三篇04-07
汪曾祺小說的風格特色如何07-30
汪曾祺小說的藝術特色分析02-28
汪曾祺小說《故鄉人》04-08
汪曾祺小說《星期天》07-15
汪曾祺小說《曇花·鶴和鬼火》04-08